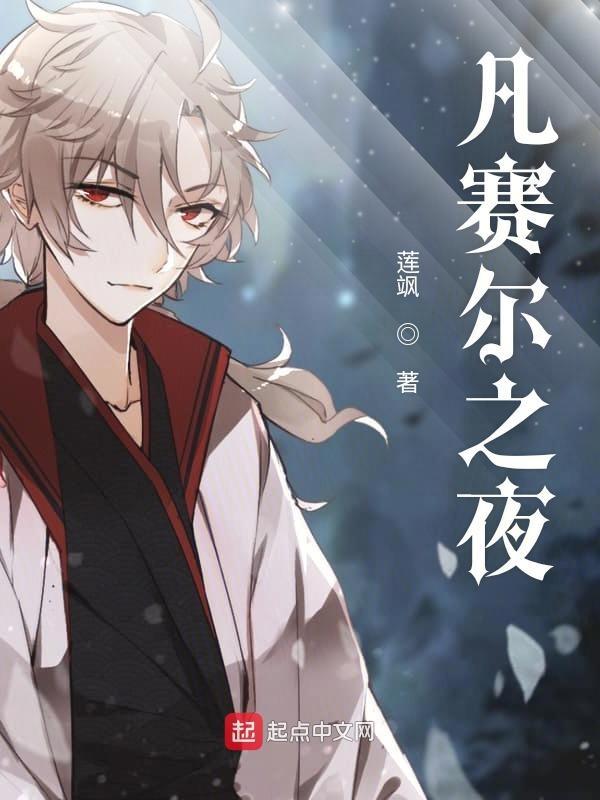夏季小说网>高危人格扮演守则男主叫什么 > 第 224 章 224 时虞(第1页)
第 224 章 224 时虞(第1页)
将地上碎成两半的金属面具捡起,简单拼凑完整,又勉强带回脸上。
时虞伸手关闭中央室内的所有运行着的设备,释千的影像消失在一片灰暗之中。她转身离开,顺着长亮的走廊一路前行。
她对这里熟到闭着眼都能去往任何她想去的地方,她也在这里享有最高的权力。
任何人——哪怕是某个财团的最高领导人,进入研究中心,就相当于将自身的生死权递交到她的手中。她在这里做出的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。
只要在研究中心,她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。
在这里,除了“编号4000”,不存在任何她没有权利杀死的生物。
在最开始那些无趣的时光里,时虞并未质疑过自己的使命,理所当然地将全部精力投入“编号4000”的计划之中。
不和任何财团勾结、也不偏颇任何一方势力。
几乎没有经历任何系统培训、在接任前完全靠观察与自我探索,时虞拥有一套堪称冷血、强控却又多变的管理模式,但她本身即是规则,所有人除了不断地服从外别无办法。
“好可怕。”
几乎所有研究中心的员工都在私下这样评价她。
“好可怜。”
编号4000却这样对她说。
那是一个多月前的释千,那个月的她状态十分和煦、没有展现出任何攻击性,甚至会和研究员闲聊一些无趣的话题,也会把无聊的电影倒回去看第二遍。
凌晨的钟声在逼近,监控里的释千看起来昏昏欲睡,却还在看那已经看过一遍的无聊文艺片。
时虞知道,释千这次如果闭上眼、再次睁开时就会忘记一切。
大概是因为这一轮的释千太过温和,也大概是因为长久一个人独角戏一样的凝视,时虞第一次亲自出现在释千的房间内,近乎鬼使神差。
将身份亮明,时虞本以为这是她们二人可以将话题聊得更深入的筹码,然而释千却说——“好可怜。”
时虞完全没想到会得到这三个字。
“可怜?”
她从没想过这两个字会和她有任何关系,目光落在释千没有自由的躯体上。她反问道,“你是在说我吗?”
语言与姿态都带着些尖锐。
这是精神层面受到攻击后下意识的自卫反应。
“你是因为喜欢你所说的、你现在拥有的那些权力,所以来到这里的吗?”释千的目光落回屏幕上,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,也像完全没感受到她的尖锐,而是不断地做出假设,“或者,你像伏源一样因为喜欢我而来;或者,你是因为我具备足够高的研究价值、可以满足你探索的欲望而来。”
时虞也清晰地意识到,由于知道释千将失忆,所以为了建立谈话地位她说了很多。可现在想来,她说出地话,通篇都只有结果,而没有动机。
聊天不仅要看别人说了什么,更要看对方没说什么。
她没办法回答释千提出的假设,她意识到她的确不存在任何“动机”。
“我不需要告诉你我‘为了什么而来’。”时虞回答。
释千笑着看向她:“你刚才想说,可怜的其实是我,对吧?那你猜猜看,我真的是被你们困在这里的吗?”
“我们是合作关系。”时虞用研究员的惯常话术回答。
“这种话记录在你们的谈话记录里就行了。”释千再次将目光放回电影上,看着屏幕上的飞鸟空镜,说,“这只鸟在自由地飞翔。”
时虞也看向屏幕。
这部电影她随着释千的视角已经看过一次了,是个十分俗套的文艺片。
滥用空镜,自认为高级、是那无病呻吟主角的内心之镜,比如这只孤零零的飞鸟,按照概念解析来分析,表达了主角耽于孤寂、又向往灵魂自由的内心。
很显然,在田埂上仰望的主角在羡慕这只飞鸟,这是主角的视角。
主角是个“诗人”,一个被周围人厌弃、嫌恶与不理解的诗人,身体被困在逃不出的田野中,精神被困在愚昧无知的思想荒漠里。
时虞蓦地意识到释千为什么把这部电影看第二遍了,就像释千用的那个词——“困”。
她说:“嗯,你也想要自由?”
时虞不得不承认,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多少带有恶意:为了回馈那句“好可怜”。
然而释千好像依旧没有意识到她话语中的恶意,反而笑意更甚,她偏头:“你觉得这只鸟是自由的?”
难道不是吗?
这只鸟在这部电影里代表的就是“自由”,主角凝视的、向往的、追求的自由。
“可事实上,它的世界就只有屏幕这么大。”被裹在束缚衣里的释千扬了扬下巴,“是啊,在它的视野里,它是自由的。只可惜,是在这个永远无法突破的框里。”
那飞鸟不断地往上飞,镜头也不断地向上移。
它在自由地飞翔,可它永远也触碰不到屏幕的边缘,甚至,它根本不知道“屏幕边缘”的存在。
当意识到这一点时,辽阔的天空空镜忽然就被压缩到很小。
而下一秒,释千的目光则再次落在她的身上,她说:“我是不想离开这里。而你,是真的离不开这里。”
她又一次展露笑容:“不过在这个框里,你是自由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