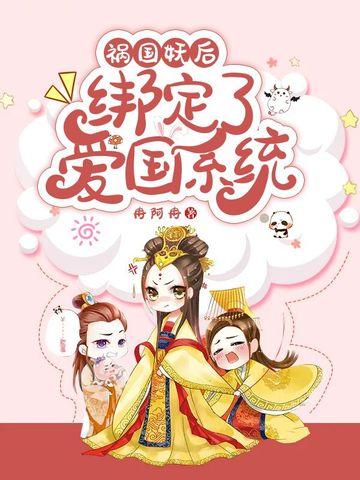夏季小说网>得了怪病的男人们免费 > 第35章 跟踪狂 揭露他的真面目(第2页)
第35章 跟踪狂 揭露他的真面目(第2页)
一遍遍地开门丶关门。随後砰的一声,他们包厢的门被踹开了。
沈鹤眠气喘吁吁地看着她,外套因为刚刚在她家时太暖和就脱掉了,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针织衫,领口处沁着薄汗。
南陆把星星重新揣回兜里。
屋子里安静下来,只能听见呼吸声。助理见没能拦住他,索性也收了手,忐忑地望向沈芸晴。
滚烫的茶气袅袅如烟,沈芸晴抿了口茶,“跪下。”
沈鹤眠这才将视线转到她身上,那张照片就摆在桌角,淫。靡地宣告着他的罪行。
其实,沈晴芸的态度,对南陆而言还是有点平淡了,和她想象的不太一样,都没有哭着求她放过自己的儿子呢。不过,她能看出她克制面容之下的怒气,也就勉勉强强开心了一点。
厢房里安静地落针可闻,沈鹤眠慢慢弯下膝盖,跪在红色的地毯上,双手垂在两边,什麽都没说。
“这些照片真是你拍的?”
她指的是南陆从小到大的照片,是里面最轻的罪证。
沈鹤眠的视线扫过那些证据,声音听不出情绪,“是我。”
“你跟我要的两年就是为了干这种事?”沈芸晴音调不可抑制地拔高,又被压了下去,显得有些咬牙切齿,“你跟你那个不着调的爹一样,我养你二十多年到底有什麽用,不知轻重,任性妄为,又蠢又恶心。”
“是。”他接的不假思索。
干脆地像是承认了他和他爸爸一脉相承,这反而像是对母亲的挑衅,惹得沈芸晴将整个茶杯都砸向了他。
好在杯子里的水放了一会儿已经有点凉了,血顺着茶水殷殷留下来,滴在他的毛衣上。
“晚上回家一趟!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
“南小姐,让你看笑话了,先前的话我都记着,定会好好管教这个逆子。”她踩着高跟鞋微微一笑,如来时依然高扬着头颅离开,步伐坚定果断。
她把跟踪狂和受害者留在一起。
让儿子自己处理掉麻烦吗?南陆觉得自己失误了。
不过幸好,她有带电击器和小刀,也在来之前报备了自己的位置。定时邮件设在下午六点半,如果她出不去,照片和视频会发给公司里的所有人。或许应该先以此和他谈判。
她握紧电击器把手,目不转睛地盯着沈鹤眠。
门合上後,沈鹤眠擡手,用衣袖轻轻蹭掉额头上的血迹,好像什麽都没发生过,起身语气如常,“这家餐厅合你口味吗?你喜欢吗?”
……她还没尝到菜是什麽滋味。
不过茶不错。
沈鹤眠走过来,蹲在她面前,“怎麽了,为什麽皱眉,和你预料的不一样吗?还好你没有约见我父亲,否则他不仅不会如你所愿,还会支持我。”
那双眼睛温和宁静,像散发着光辉的曜石,让人生出想扒出来擦一擦,擦掉上面虚僞的平静雾色,露出脆弱不堪的内里。
沈鹤眠将手搭在座椅,食指关节轻轻蹭着南陆的衣服口袋,发觉南陆并不排斥以後,得寸进尺地塞进她兜里,和她十指紧扣。
直到这种时候,南陆才清楚的认识到,他真的是个疯子。
但她同时也很失望,很糟糕的感觉,让她觉得自己演了一部烂尾剧。
“你怎麽不哭?”南陆将电击器扔到一边,抽出纸巾,缓缓擦拭不断滴落的血水。
濡湿的舌尖划过手腕,被吮出浅粉色的印记。他将南陆的手贴在脸上,“我不知道,或许我的眼睛只愿意在床上哭。”
车子停在楼下,南陆坐进了副驾驶,沈鹤眠嘱咐她,“最近不要去上班了。”
父亲的上一任情人以悲惨的死法谢幕,沈鹤眠现在还记得泳池里泡得发白不着寸缕的尸体。向来风度翩翩的父亲吓得跌倒在地涕泗横流,却在不久之後又找了新欢。
不知道南陆有没有听进去,她靠在车窗玻璃上,肉眼可见的沮丧。
是难得的鲜活表情。
到了楼下,沈鹤眠想先下车,被南陆扯住衣袖,她跨坐在他身上,放平了座椅,指腹按压在他的喉结之上,没用什麽力气,但确实影响呼吸。
“你应该哭啊。”
沈鹤眠没有反抗,他握住南陆的手,恨不得让南陆现在就掐死自己,脸上甚至因为想象而泛起病态的潮红。
“我该怎麽哭呢?”他问。
南陆也不知道,但总之她很烦躁,尤其是他跪在他妈妈面前时,那盏茶水砸到他额头时,他不冷不淡地承认罪行时,那种烦躁感层层叠叠的积累。
他得先去止血。
“把我欺负哭吧,按你想做的那样。”他扣住她的手,力道逐渐加重。
“……”